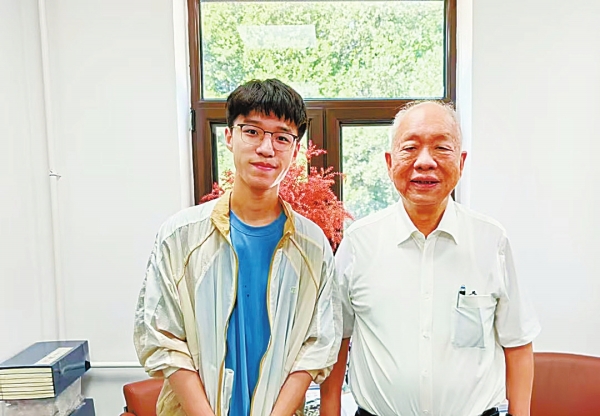
本文作者與丘成桐先生在一起。通訊員 攝
吉翔
八月的熱浪裹挾著南國的潮氣,我站在皇崗口岸的晨光中,視線投向那片承載著丘成桐先生生命密碼的土地。
這是我們探訪的第一站,也是1949年出生才數月的丘成桐登陸香港的第一程。彼時,為避戰亂,父母懷抱他從故鄉廣東汕頭來到元朗。從此,異鄉成為故鄉。
白田、排頭村、下禾輋、龍鳳臺……我立于靠山面海處,想象當年那個在溪澗中游泳嬉戲的活潑少年,他的純凈、可愛與青澀模樣。丘家8個子女長期擁擠于陋室,歷經多次輾轉搬遷。租住的“牛屎屋”邊的小廣場上,連同丘成桐自制的風箏一起放飛的,還有父母辛勤操持下一家人其樂融融的“窮快活”。
母親繡花、做塑料花,兒子挑水、種地。饑餓是丘家長久的底色,丘父丘鎮英先生卻在油燈下展開《論語》《楚辭》,將中國古典文學的星火植入兒子心田,蘇軾大江東去的磅礴、陶淵明田園詩話的鄉村風味,在少年丘成桐心中扎根。丘成桐讀了《紅樓夢》10遍,自此沉浸在文學、哲學里的人生百味。錢穆先生與父親丘鎮英在西林寺飲茶論道時,少年丘成桐侍立一旁端茶倒水、洗耳恭聽。
丘鎮英于油燈下開啟的并非僅僅是知識的傳授,更是哲學視野的啟蒙。“整體地看歷史”的宏觀格局,后來奇妙地轉化為丘成桐攻克“卡拉比猜想”時俯瞰數學宇宙的思維范式。文學經典的浸潤、哲學思辨的滋養,使他的科學探索獲得了深邃的人文根基與恢弘的宇宙意識。
丘父去世后,丘母梁若琳老太太——那位被沉重生活壓彎脊梁卻百折不撓的偉大母親——在安葬好丈夫后,心中盤算的只有如何讓孩子們不輟學,要為孩子們筑起遮風擋雨的屋檐。火炭村拔子窩的自建小屋,成為丘家結束漂泊的方舟,自此丘成桐先生有了第一個“家”,它見證了一個中學少年郎在喪父劇痛中徹夜攻讀專業課程后研讀《史記》《資治通鑒》的身影。古典文字里先賢的堅韌不拔,成為他抵御現實寒夜的薪火與光明。
我來到這里,將丘成桐先生書中的文字與照片相對照,試圖找到丘先生的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家。雜樹蔥蘢,新屋有主。老房子已不在了,新的主人在此重建。只見一株古老的龍眼樹枝繁葉茂、碩果累累,我猜測,這是少年丘成桐先生所植。
我幡然頓悟,家,是父親哲學燭照下的思維格局,是母親以血淚澆灌的生存意志。此“家”已超越物理空間,升華為一種精神的圖騰——融合了父親的哲思高度與母親的生命強度,奠定了丘成桐先生“做人”與“求學”的堅實基石。
行路,讀書。一邊翻讀丘成桐先生的書,一邊追尋丘成桐先生曾經的人生路,心間奔涌的能量噴薄而出——茍真理之可知,雖九死其猶未悔。
在丘成桐先生大學母校——香港中文大學的馬料水,風景十分壯麗。在這里,丘成桐先生得到學校關愛、名師指點,他勤奮苦讀,提前一年大學畢業。后他又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,22歲獲得博士學位,開啟他在數學王國的遨游。后來廣為人知的是,他成為哈佛大學數學系和物理系終身教授,是該校歷史上唯一同時擔任兩系終身教授的學者,并在32歲時成為第一位獲得有“數學諾貝爾獎”之稱的“菲爾茲獎”的華人。1994年,他為了回報母校,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并擔任所長。
今天,我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山頂的合一亭,只見山海遼闊壯美,晚來的風雨褪去酷熱,亦洗盡鉛華。
我想起了鄉人的一句詩:當桐葉茂盛/鳳凰棲梧桐/抖落一場好雨。丘成桐先生為之奮斗的理想,不正是這樣的寫照嗎?
丘成桐先生曾在書中表達:父親留下的哲學智慧與母親的堅毅力量,是他收到的最珍貴遺產。這份遺產不在物質,而在于苦難中淬煉出的雙重能力——既能在數學宇宙中攻克恢弘的猜想,亦能在人世間鑄造士人的高風。
人們不會忘記,丘成桐先生為人類科學與教育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。他在清華大學等眾多學術機構創建的數學中心,以及雨后春筍般涌現的“丘成桐班”,可謂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。
責編:歐小雷
一審:歐小雷
二審:印奕帆
三審:譚登
來源:華聲在線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