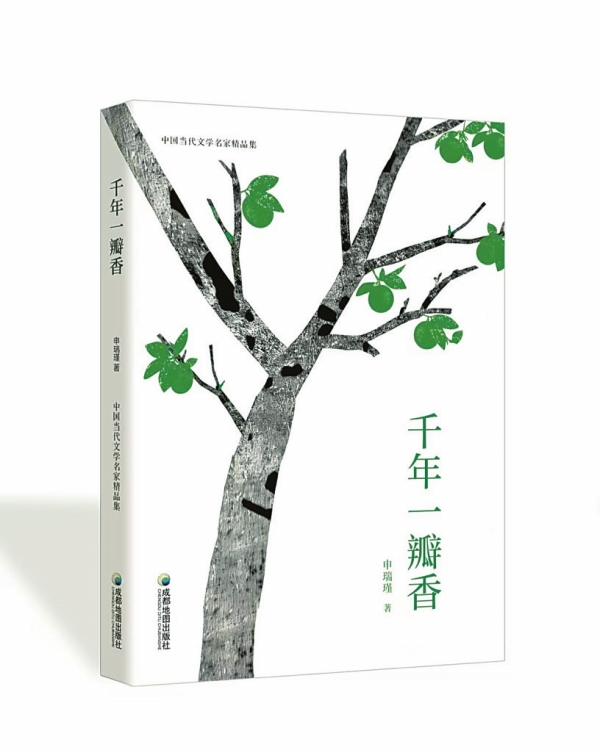
賀有德
申瑞瑾的散文,之前只是零散讀過。直到今年五月,成都地圖出版社出版其散文集《千年一瓣香》,我才有意識地沉潛式系統閱讀,手不釋卷,如品香茗。
我們有過多次交流,有兩次印象極深:第一次,無意中談及自己的散文創作,申瑞瑾坦言“寫得慢”,不是倚馬可待的那種,喜歡“精打細算”,寧精毋雜,寧缺毋濫;另一次,探討對散文創作的追求,申瑞瑾力主不妨“寫得野”,不喜歡四平八穩的寫法。這兩條,成為《千年一瓣香》的“指揮棒”與“定海神針”;也是這兩條,將《千年一瓣香》推向了一個散文的新高度、新境界。
全書分兩輯,前一輯“千年一瓣香”為山水篇,可稱為“行走散文”,行走北國江南,以筆為杖,丈量天地,以手中筆寫眼前景,“我”無處不在,“以我觀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;后一輯“人在草木間”仍然是“行走散文”,主題從山水風物的欣賞轉為茶文化的探究和傳承,兼及親情或鄉愁,多角度多層次書寫“我”之所見所聞所思,讀來“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”。
申瑞瑾的“行走散文”,不走流行路線,不是走馬觀花,也不是淺嘗輒止,而是用心用情用功。也正因此,《千年一瓣香》有著鮮明的個性,如一股清流肆意流淌,直抵人心深處。
前一輯中,從江西南豐到內蒙古呼倫貝爾、新疆北天山、貴州大明屯堡、重慶西沱古鎮、湖南耒水,最后到山東日照,南來北往,山水遼闊,如多彩的畫卷。《北天山紀行》里,北天山、博樂、庫賽木奇克、賽里木湖、夏爾希里,風光旖旎,千姿百態;漫游山水,不止山水,插入“戍邊者的鄉愁”和“怪石峪的佛”,拓展廣度。后一輯中,則以資深茶客的閱歷和眼光觀茶、品茶、說茶,《四水尋茶》《從茶蕩漾開去》《茶與故人》《走在春天的茶香里》《春風里飄過最早的茶香》諸篇,“茶”是主角,標題詩情畫意濃郁,恍惚間有茶香飄來。每一次說茶,科普茶,也著眼廣度,以“茶”為線索鋪陳。比如《四水尋茶》,以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水為依托或載體,從面到點,“冰糖葫蘆式”一一呈現;又從點到面,圓形結構收束。每一處寫茶,既從不同地點著筆,又從不同門類分述——比如寫湘水的茶文化,涉及永州、郴州、衡陽、株洲、雙峰、湘潭,每一處又分門別類書寫,寫法不循常規,仿佛茶文化寶典,引領讀者在博大精深的茶道里穿越,讓人大開眼界。
游歷山水,品味茗茶,在著眼廣度的同時,彰顯出不尋常的深度。
前一輯開篇《千年一瓣香》以南豐蜜橘為引子,引出對曾氏家族千年家風和文脈傳承;以“異香”為線索或明或暗貫穿始終,主體仍是曾氏家族,旁及大宋文壇大佬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東坡,由曾鞏串聯起“文人相親”的文壇佳話。南豐蜜橘只是引子,或者隱喻,借此由物及人,哲理探究水到渠成——“我們頂禮膜拜的不僅是珠璣文字,更是文字背后所折射的文人之間的人性光芒”。后一輯寫茶文化,功課做得更足,更見深度。申瑞瑾自言曾“應約寫《美麗瀟湘·茶事卷》”,因而“翻閱大量相關資料”(《從茶蕩漾開去》);不止如此,“每每品到一款好綠茶,我會下意識地去查茶產地的緯度”(《春風里飄過最早的茶香》)。《四水尋茶》縱向深入,引經據典,條分縷析,歷史文化底蘊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廣度與深度的雙向交融,“行走散文”便超越了一眾泛濫成災的游記散文的單向模式或者說單一化,別開生面,厚重、深邃。
申瑞瑾是性情中人,真性情文字,有發自內心的質樸和真誠,有一種別樣的溫度在。讀《千年一瓣香》,最適宜的,是在出門游歷的路上,或者居家品茗的閑暇。東行,西去,南下,北上,游歷名山大川,穿越大街小巷,展卷把玩,如品香茗;若無閑事掛心頭,或者忙里偷閑,潛心品味,你會不知不覺在春天的茶香里沉迷……
責編:歐小雷
一審:歐小雷
二審:印奕帆
三審:譚登
來源:華聲在線








